2006年×月×日
昨天睡得很好,早上醒来已是10点以后,火车已过宝鸡。车窗外满是黄土高坡,我有许多年没到过这一线,大约中午12点45分到达兰州。沿途许多地方都是裸土、裸沙,环境明显的风沙很大。黄土地上的房屋多半是乡土砖房,房的式样与内地的有些不同,绿化很少。星星点点的树木很少成林,杨树比较多。黄河水很少,黄黄的,象南方的一道小河。西北缺水,导致植被不好。
河西走廊,古时候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。被称为丝绸之路。现在一路走来,感觉到的却是一个干字。缺水少雨,风沙横行。这里山上有沙丘、黄土,河谷中有些地方的牧草地也在开始沙化了。地面上大片的平坝上只看见稀稀拉拉的一点小草,而且草低矮得可怜,这里真成了不毛之地。偶尔也看见一块水泽,那里草要长得好一些,离水远一些就不行了。越往西行,人烟越少。
我出发前感冒一直未好,今天好象感冒症状轻一些,不鼻塞,但喉咙有点干痒,这大概与西北干燥的气候有关。室外温度39°,看来西北也不凉爽。
远处的沙山呈现出流畅的曲线,沙山光秃秃的,灰红的沙丘一个连着一个,绵延起伏,永远的没完没了。望着沙丘连绵,画面虽然奇异,可心里却不轻松。西北的沙漠是著名的不毛之地,柴达木盆地也是著名的沙漠盐碱地。我前年去从美国拉斯维加斯往洛山机途中,沙漠荒地连绵不断,可是美国人对沙漠的治理已见成效,沙漠上已长了草,草团连着草团,一直连到山坡上。看来,沙漠绿化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火车路过一个很大的湖,远远地,有人说那是青海湖,我不知道是不是。看那巨大的湖的规模,也许是吧。湖的对岸是重峦叠峰的沙山,连绵不绝。近岸是草地,湖水蓝蓝的一片,近处的草地不是那种鲜绿色,而是老绿色,色彩绿中带灰。地表沟沟坎坎,并不平顺,也不柔和,而有一种粗野狂厉之风格。草长得粗壮,这是我见到了西北牧草的第一印象。这种草的与江南的绿草相去甚远。西北的粗犷野道的格调与这里的气候自然条件是一致的。能够在沙漠连绵的群山之间生长的草甸,那顽固的生命力是可想而知的,这种旺盛生命力也注入西北人的生命河流中。
河谷一段一段的不同,有些河谷也出现农舍。农舍外除了青稞之外,还有油菜花,大片大片的。这里的油菜花有些老橙黄色,金黄中有些土色。油菜和青稞地一望无际。田野里有一些土墙,只有墙没有屋顶,而且一段一段的并不完整,有些地方已经垮塌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土墙呢,是建筑吗?也许是关围牛羊用的围墙,好象也不完整。有时在大片的草地深处也有高耸起来的黄土建筑,也是看不到顶,但比围墙高,范围没那么大,也不是古代遗迹。有些地方的土墙高高低低,的确象房子,同样没顶。也许,这里过去有人,现在已经搬迁了,可庄稼还在,人去了哪里呢,想不清楚。
有许多地方几乎无人存在。丘陵一般的高山草甸青一块紫一块,象受了伤的肌肤。这时黄昏来临,长长的,远远地拖着的山的影子,只有高处才显得出残阳斜照。草原则变成了一遍暗色阴影,红光都集中到山峦的高处。残阳如血泻在神秘的极远处,望着这艳丽无比的美景,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中,不知人们是被眼前的日落所吸引,还是荒原的寂寞带给旅途的人们莫名的沉思和伤感。大地黑暗了,天空也暗淡了,只有云彩间的一丝残红以及沼泽反光的微白还清渐可见,山峦和天空之间还残留着一条隐约的分界线。
当火车过了西宁,穿过柴达木盆地的边缘,一路西行到达格尔木,这一线已是在青藏高原上行驶了。格尔木海拔已经三千多米。车上没有供氧,微微地有些感到缺氧。
申老师的女儿叶子,特别爱动,是这次唯一的一位小孩。记得上次去东南亚时,她那时二岁,一路上男孩们顽皮,耍得野。叶子很小,追着男孩们要和他们玩。那时的叶子,走路不稳,一晃一晃的。可几年过去,如今再见到叶子时模样大变,小姑娘身材苗条,吸收了他父母的优点,已出落成一位漂亮的小公主。在火车上,叶子特别喜欢与唐叔叔玩,要唐叔叔玩骑马马。所谓骑马马,也就是骑在唐叔叔的脖子上让唐叔叔托着她在车厢过道上跑。叶子高兴得哈哈大笑。这有点象西藏古代的王子,人们让王子骑在脖子上,簇拥着来到众人面前。可火车上过道空间太矮,唐叔叔只能曲膝弯腰托着叶子往前跑。跑一会就累了,放下叶子,告诉她叔叔累了,休息一会。叶子去玩了一会别的,跑来问:
“唐叔叔,休息好没有?”
“还没有。” 唐叔叔回答。
过了一会叶子又跑来问:
“唐叔叔,休息好了没有?”
“还没有。”唐叔叔悄悄地笑了。
叶子又跑去玩别的了。后来到了格尔木车站,下车到了月台上,叶子又骑上唐叔叔的脖子,他们跑得真欢。那里空间高,唐叔叔挺直了腰杆,象草原上真正的大马一样奔驰。叶子银铃似的笑声在高原月台上响成一串。童年的欢乐飘洒在高原上,变得更加欢快自由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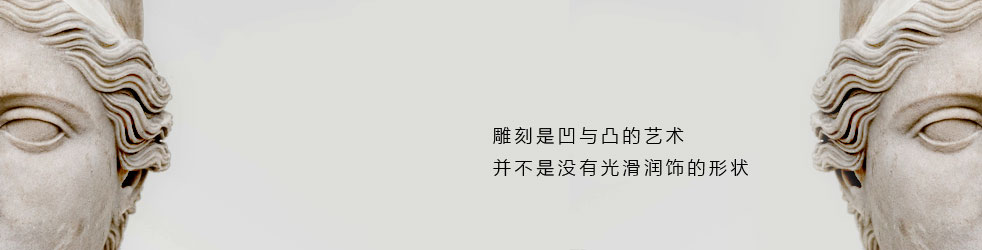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
请登录